2021年11月25日刊|总第2699期
由埃德加·赖特执导的电影《Soho区惊魂夜》与观众见面了。

不过就《Soho区惊魂夜》而言,大众的接受程度或许会更高。它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怀揣着梦想进入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们达成了契合。
是娜拉,也是于连
之后,鲁迅又写下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文。在他看来,娜拉出走的结局无外乎两类:要么堕落而死,要么平庸而归。社会上,男女势力不均等,致使男女经济分配不均衡,出走后的娜拉又靠什么谋生呢?
虽说,只要有一定的学识和才能,现代社会里的女性不至于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除了为钱离家外,如今的女性还怀揣着闯出一片天的梦想。新世纪的“娜拉”们解决了“老娜拉”们糊口难的问题,可精神危机仍在等待着她们。《Soho区惊魂夜》里的爱洛伊斯(托马辛·麦肯齐 饰)便在人生的岔口遇上这一烦心事。

爱洛伊斯是个对时装充满激情的小镇女孩。心灵手巧的她平日自己设计衣服,对上世纪60年代流行乐备感兴趣。
好在老天眷顾,她被伦敦时装学院录取。欣喜若狂的爱洛伊斯带着塞满音乐唱片的箱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标配,不是象征物质的衣物,而是由艺术支撑的精神食粮),坐上去伦敦的列车。

除了男性将女性的梦想客体化(被审视、把玩的性商品)外,都市里的“本地女性”对外来姑娘也怀有敌意,这主要源于爱洛伊斯的怀旧属性与都市女孩现代性的、未来感十足的时尚审美差异。
浑身上下全是名牌的室友,把爱洛伊斯的怀旧、勤奋,看作一种过时的、老土的、蛮干的乡巴佬特质。都市借助不同的审美取向,向外来者关上大门。

都市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侵害,还体现在爱洛伊斯的母亲,以及神秘女子珊迪(安雅·泰勒-乔伊 饰)身上。

“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也曾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遍体鳞伤,才知道原来我们都只是草。”爱洛伊斯也好,当下于都市打拼的“社畜”也罢,都经历过这种体验:本以为是精神上的巨人,结果却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

虽说《Soho区惊魂夜》反映了身份的游离、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但导演埃德加·赖特并没有采取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和影像语言,而是以心理惊悚片的模式进行叙述。
是波兰斯基,也是埃德加·赖特
如无脸男性鬼魂群像,就借鉴了《灵魂狂欢节》;爱洛伊斯“看见鬼魂”的设定,既像做梦又像阴阳眼,近似于《威尼斯疑魂》中的灵媒;珊迪与爱洛伊斯的多重镜像,则致敬了今敏的《红辣椒》。而在主旨设定上,本片主要沿袭了罗曼·波兰斯基电影中“局外人”的表述。

上图:《Soho区惊魂夜》;下图:《灵魂狂欢节》

上图:《Soho区惊魂夜》;下图:《红辣椒》

同时,爱洛伊斯也具有疑神疑鬼的病症。她觉得自己正在被鬼怪追赶,透过天花板上的玻璃看到珊迪被杰克杀害,并怀疑酒吧神秘老人(特伦斯·斯坦普 饰)就是逍遥法外的杰克。爱洛伊斯真假难辨的幻想,极易令人联想到《冷血惊魂》中的妹妹:一个呆在屋里肆意联想,最终精神崩溃的女人。
正是这种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为《Soho区惊魂夜》增添一丝心理惊悚片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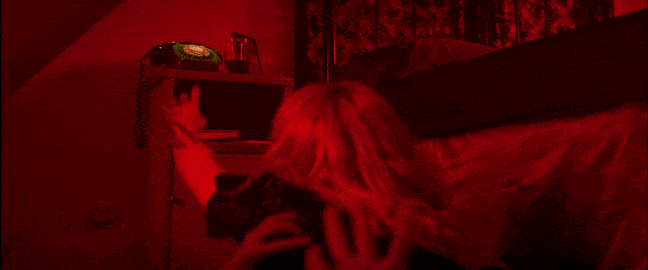
在塑造爱洛伊斯的幻境时,影片通过镜像以及不同人物的转场,来构建梦境化场景。
片中爱洛伊斯与珊迪是并置在一起的。一开始,观众都不能明确二者的关系,甚至以为珊迪就是爱洛伊斯的另一重人格。通过镜像,两个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女人合二为一,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此外,“三人同舞”令人记忆犹新。看似是珊迪与杰克跳舞,但借助影像上杰克身躯的遮挡,以及其他舞者的转场,杰克时而与珊迪调情,时而与爱洛伊斯共舞,传递出影像上的随意性与美感。

除了构建人物内在环境外,埃德加·赖特还通过画面讲故事,暗示剧情走向。
当驶向伦敦的列车进入隧道时,车窗外的世界一片漆黑,爱洛伊斯也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伦敦的生活到底是她梦想成真的天堂,还是外婆口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人间地狱?对爱洛伊斯而言,这些都是未知数。

爱洛伊斯以为是杰克一帮人杀了珊迪,谁知结尾有个反转,被害人成了施害者。尽管如此,开头、结尾构图上的相似性,亦暗示女性在当下社会里被压制的宿命。

音乐和舞蹈也是本片的一大亮点。这种金曲串烧,并非《银河护卫队》那种纯怀旧向的展示型配乐,而是对人物状态、行为动作有一定暗示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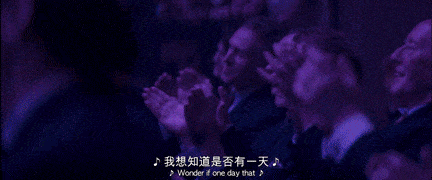
结尾,年老的珊迪葬身火海,爱洛伊斯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说埃德加·赖特用了一个俗套的结局,但《Soho区惊魂夜》里的思考仍具有现实意义: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在当下,又有多少娜拉,多少于连呢?
【文/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