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人世间》里,增加了一个小说里没有表现的年份:1981年。
在梁晓声的原著里,《人世间》三册的时间,并不具有连贯性。上部从1972年——1976年,写的是文革年代。中部描写的是八十年代。下部是从2001年之后开始描写到2016年,可以称之为新世纪篇章。
在《人世间》中部的时间段里,叙事时间直接跳到了1986年,中间的几个年代,在小说里都是作了跳跃式的概略式描写。
而在电视剧中,则重点选择了几个表现的年代。
电视剧中的八十年代时间段,有1978年,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可以说是按照“城春草木深”的梯次逐级描写的。

1981年的故事,在小说里是没有表现的,这给电视剧改编者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而1981年的最大的人物关系的变化,就是郝省长官复原职,当了省长,剧中说,省委书记身体不好,郝省长是党政一把抓,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为什么要在电视剧里出现原来小说中早已去世的郝省长?
因为电视剧需要用这个人物,来衬托秉义的大爱。
在《人世间》小说中,秉义不徇私情,面对家人的求助,秉义是公事公办,没有给予额外的照顾。
为此,秉昆对秉义十分不满,认为他忘恩负义,不讲情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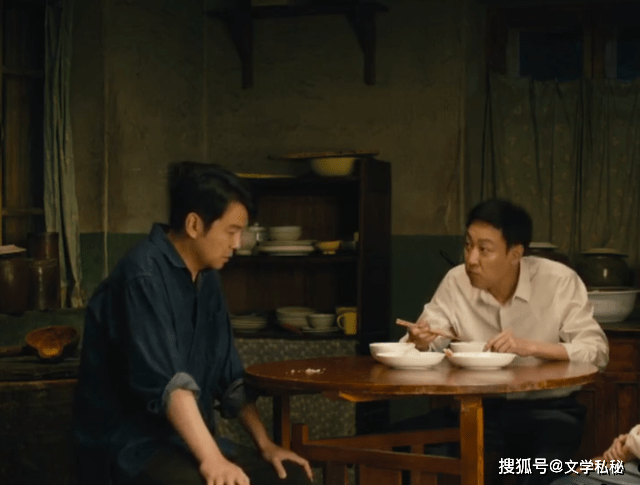
《人世间》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就是秉昆有情有义,照顾老人,关爱孩子,秉义则是一心当官,对家庭不闻不问,其实,在秉义的身上,更体现着一种大爱的精神。
什么叫大爱?
那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把国家的为民政策做好做足,造福于民。
在小说里,孙赶超的妹妹并没有名字,电视剧里取名叫孙小宁,并添加了一段她追求秉昆的戏份。这个设置是一个失败的改编。

据小说介绍,孙妹在护士学校毕业,但无法找到工作,想通过秉义,通过他的权力,能够介绍到医院里去。
但秉义却直接予以拒绝了:“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你帮得了一个,帮得了千千万万吗?……你那种哥们儿之间的情分根本就不存在我的考虑范围!我没心事管你的事!”
秉义的貌似无情无义的回绝,令秉昆十分生气,回敬道:“帮不了千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了吗?滚!从我的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你这么个哥!”

后来孙妹不得不远走深圳,在小说里的命运很悲惨,患上了艾滋病,投河自尽。而电视剧里则改编得相对缓和一点,在深圳,与之前她不顾一切追求秉昆一样,也是搭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来被人家前妻赶了出来,一无所有,虽然赚了一点钱,但是觉得面上无光,给家里写了一封自决书。
秉义的看似绝情的处置方式,恰恰是郝省长夫妻俩,对周家的态度。
剧中的郝省长妻子金月姬,在1981年的时间段,与冬梅有一段激烈的争论。
这就是剧中由两罐茶叶引发的轩然大波。

这个情节,在小说里是没有的,因为1981年的这个年代,在小说里并没有详加描写。
而这个添加的1981年的戏份,正可以说是对梁晓声小说主题的一次形象化演绎,而且这个段落中的争论核心,在梁晓声的小说原著里的其它部分都有所提及。
剧中的这个冲突,可以说是把梁晓声的时代思考转化为形象冲突的一次实际操练与具体体现。

梁晓声的小说主题,就是“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对阶层在当下社会现状中的客观存在,一直是梁晓声孜孜以求加以探讨的问题,按照他的这一社会观,他用以支撑起了《人世间》里的主体人物关系冲突。
在小说中册360页中,秉义对冬梅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比较代表性地阐述了阶层的存在,以及这背后的背景纵深:“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层。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甚至憎恨的心理看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就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不等于就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家的偏见。”

梁晓声说得相当明白,“阶层”就是过去的“阶级”。
梁晓声是不是仍然沿用了阶级斗争的思考方式,认识现实社会?
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阶层”是梁晓声小说里出现的一个非常频密的词,他也曾经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为标题写过一本专著。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通过周家长子秉义的婚姻,把阶层差距摆在了一个突出位置。

这种阶层差距最醒目的表现,就是郝省长一家,从没有到过周家所在的贫民区。
小说里多次提到这种阶层的差距。
在小说中册183页写道:“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
小说里还通过周父之口,提到了与郝省长一家从没有见过面的事实。

小说里的周父看起来对亲家的谅解之词,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了周父其实是期望位高权重的郝家来看望自己的。
周父对郝家不来探望的一段自我解释,在电视剧中就演化成了1981年春节段落中的一段重场戏。
在这个场景中,出现了郝省长。
郝省长的出现,显然改变了小说里的既有设定。在小说的氛围里,冬梅的父亲郝省长已经去世,只有母亲,而母亲已经退休,这为郝冬梅的母亲没有来到周家探望提供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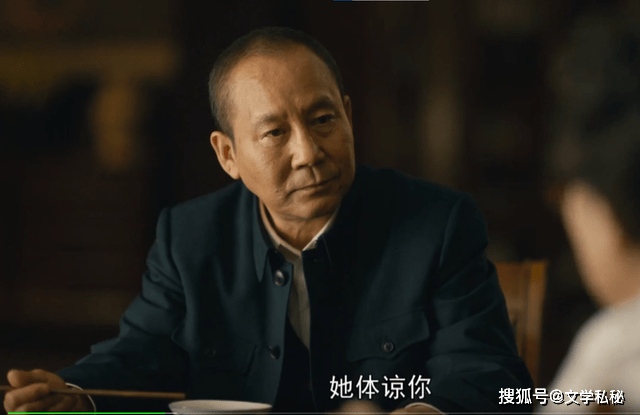
但现在电视剧的设定改变了,郝省长健在,那么,作为一家之长的郝省长,且作为一个男性,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来周家看望。
电视剧正是这样表现的。在1981年春节,郝省长已经确定了到周家拜年的计划,也让周家一大家人充满了期待,但是,郝父突然生病,使得登门拜访计划夭折。
其实,这时候电视剧已经绑架了小说原著。电视剧增加了郝省长,但是现在郝省长突发意外,生病住院,那么相应地,周家人不应该赶到医院或者是郝家来探视一下吗?

在小说里因为郝省长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不存在周家一大家看望郝省长的情节,但现在电视剧里出现了郝省长,而且郝省长准备去看望周家了,还由黄秘书送去了看视礼物,作为中国礼尚往来的习俗,周父带领一家人,去看望郝省长不是应该的吗?
这就是电视剧擅自改编了原小说里的设定所导致的情节不合理的尴尬所在。
电视剧里,郝省长深知周家所在的贫民区的破败现状,也企图改善这片贫民区居民生活状况,在剧中,他特意说要一步一步地解决。
可见,要改变民众的生活面貌与生存状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政策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而这也正是梁晓声在小说里分析社会进步时所着意强调的一点。
在小说下册第435页这样写道:“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这样,秉昆身边的底层人士的相互帮助,便只能说是一种“小爱”,更大的大爱,是国家体系所施予民众的实质性的影响。
这样,我们可以从《人世间》里秉义与秉昆之间的地位的反差,看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高度,散发着不尽相同的爱的光芒。

在秉昆的生存空间里,每年他与工友们的聚会,不过是借这种聚会来联络感情,巩固友情,然后打造一种可以相互帮扶的“人情关系”。
梁晓声充分肯定了这种“人情关系”对于底层民众的重要意义。
在小说中册194页,作者这样议论道:“人情关系是人类社会通则。……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
丑恶的人情关系主要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多少人情可言。”

在这种底层人士抱团取暖的人情关系中,作者表现了小说主体着意刻画的社会众生相。
梁晓声肯定了这种底层民众的相互关爱所带来的价值与意义,而小说的感人部分也是通过摹写这个阶层来完成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社会框架下的小爱,真正的大爱,是实现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国家的强大。
这一部分就必须依靠电视剧里增添的郝省长这样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者的努力来实现与完成了。

郝省长并没有完成这一个任务,他也知道周家所在的贫民区的民众生存现状,但他受制于他的时代与个人的身份,并没有实现他倾其一生期望实现的使命。
而这个使命由他的女婿秉义来完成了。
秉义在小说中,屡屡对家里的亲朋好友提出的帮忙请求,予以拒绝,甚至让弟弟十分恼怒,恶语相加,斥责他不近人情。
相反,善解人意的周蓉却非常理解秉义的这种弃小义、奔大义的行事态度。

《人世间》中册223页里,周蓉有一段对秉昆的长篇说辞,阐述了秉义的精神质地,主要内容择要如下:“从根本上说,他不属于嫂子,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自己。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组织的人。……以后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他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
周蓉是梁晓声笔下情商与智商非常高的一个人,如果说是最高的一个人,也不应该有异议。
但正是这个看得太透的人,却被观众解读出自私的定性,实在是一件非常出人意料的事。

包括梁晓声也可能徒呼奈何。
秉义后来在自己的市委书记的任上,一手操作了贫民区的改造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稍稍地利用特权,让秉昆从旧房改造中多沾了一点便宜。
秉昆对自己的老宅,不过是修修补补,维护维护,但没有改变家里的住房面貌,而秉义从根本上铲除了“苦根”,改善了郝省长为代表的上一代人没有完成的改善民生的良善愿望。
这就是大爱与小爱的区别。

所以秉义与秉昆两个人物的形象上,还是寄予了梁晓声源于阶层理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而梁晓声更为可贵的地方,是肯定了“大爱”才是社会面貌发生改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电视剧中,郝省长与秉义通过女儿的婚姻关系勾连起的一条关系脉络,撑起了“大爱”的与时代相合拍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仅仅是前台秉昆的“好人之爱”,是不足以完成整个小说与电视剧的价值深度的。

这就是梁晓声一方面在小说中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努力,更从全局的方面,阐述了社会进步的更为关键的那一份国家的力量。梁晓声用这部小说,作出了他对中国现状的思考,而目前来看,也是当代作家中做得如此完美的说明着中国进步之因的一个具有独特观察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