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蒙马特
近几年,有人一直在谈论「港片已死」,香港的商业片导演纷纷北上拍片,大银幕依旧是那些熟脸,偶有几部本土新导演的创作,也只是昙花一现。但香港的年轻新导演们,总带着港人的责任感和坚持,不断探索着港片的更多可能性。《一念无明》《沦落人》《金都》,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他们都离不开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支持。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
去年在金马亮相,今年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的《金都》,被媒体和影评人们一致叫好,金马影展执行长闻天祥称其「一定要看……目前香港大片绝对不敢碰的大写,在这里一目了然,抽丝剥茧中港关系,更照见自己的内心所需」,文汇报评「《金都》是一部让人笑着为香港现况唏嘘,同时有多重解读空间,久久依然回味的电影」。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真实、生猛而大胆的电影,它借由即将结婚的阿芳思考婚姻的真谛的故事,探讨了婚姻关系及自由和幸福的边界。从影18年的邓丽欣,和用18天时间的低成本预算首次拍长片的黄绮琳,联手贡献了这部今年最让人期待的港片。从那个爱情至上的「阿宝」,到《金都》里质疑结婚自由的「阿芳」,邓丽欣完成了影后级的蜕变。

而《金都》,实际上是从编剧转型导演的黄绮琳,写给港女们的「婚前箴言」。从《玛嘉烈与大卫 绿豆》的玛嘉烈,到《叹息桥》的Joyce,再到《金都》的阿芳,黄绮琳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在婚姻和爱情中徘徊的港女形象。「30岁生日这天,我突然涌起了垂死挣扎的热血」,在30岁生日当天,她开始了剧本的创作。
黄绮琳和邓丽欣
对于「适婚年龄」的女性来说,婚姻仿佛成了隐形的枷锁,我们努力地完成着父母为我们设定的人生KPI,又暗暗佩服着那些选择了不婚主义的勇士。电影却给出这样的提问:「结婚没有自由,那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

」
「金都」,在这里不再代指香港的纸醉金迷,也不是作家陈冠中笔下的《金都茶餐厅》,后者有个英文谐音「can do」,倒是调侃了香港人做生意的小聪明。而电影里的「金都」,是位于旺角太子站的金都商场,置办一切婚礼服务,包括婚纱礼服、婚礼摄影、花车、珠宝等,就在黄绮琳家的对面。
电影里,31岁的阿芳和相恋七年的男友Edward在这里上班,女生在好友阿怡的婚纱店,男生经营着一家婚礼摄影店。他们见惯了无数年轻情侣在「金都」奔向幸福的殿堂,而自己也将按部就班的结婚。

很有意思的是,《金都》的英文名为《My Prince Edward》,而阿芳却不确定男友是不是自己的王子。
婚姻有七年之痒,恋爱也是。长久的同居关系和Edward的占有欲让她感受到了爱情的消逝,婆婆的催婚、拥挤的出租屋、男友我行我素的行为和夺命连环call都让她喘不过气来。更紧要的,她心中藏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她和一个大陆男人「假结婚」十年。要想结婚,先得离婚。
十年前她为了爱情离家出走,为了付租金,铤而走险和一位陌生的大陆男子杨树伟领了证。

两人可以说是互相利用,杨树伟也是想借此拿到香港的身份证。费了好一番功夫,两人在街头相认。要想离婚可以,前提是他先拿到单程证,而发证又要证明结过婚。两人被迫「恩爱」营业,阿芳在拖住婚期焦虑办离婚的同时,不慎被Edward发现,矛盾爆发。
「假结婚」和「真结婚」在Edward的想象里正面交锋,他勃然大怒的点是,女友可以为了几万块钱和一个没有爱的人作假,也不愿和相恋七年的自己马上成真。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践踏,这种意义上的欺骗虽然不能说是「精神出轨」,但对于一个求婚时洋洋自得的妈宝男来说,犹如一场羞辱。

但是他分明是爱她的,否则不会再问「我们是不是不结婚,就得分手?」
非此即彼,人生做选择也是有固定答案的吗?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流程和步骤吗?金都大厦就是婚姻流程的象征,前来拍照的将婚男女们,甚至订婚的阿芳,都要被装在「1-2-3-4」的摄影框内,强颜欢笑地被别人记录下所谓幸福的时刻。
没有遇到突然回来的杨树伟之前,阿芳不过是个随波逐流的港女,好奇宠物店鱼缸里翻身的乌龟,被老板硬塞给她买下,还不是「那一只」。翻过身的乌龟可能要筹谋出走,但是能力有限反而把自己永远困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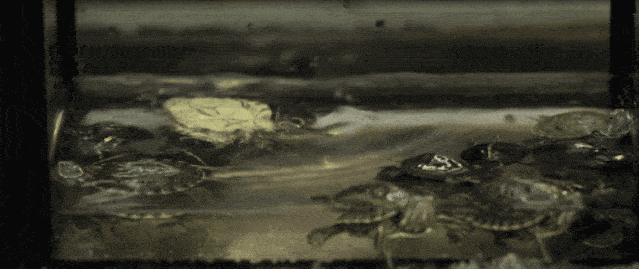
因为同处困境,阿芳和乌龟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当为了布置新房,婆婆自作主张放生了阿芳的乌龟后,阿芳和Edward激烈地争吵起来,哭诉自己没有婚姻自由,现在也失去了养龟自由。突然想起电影开头阿芳刚养龟时,Edward的预言,「你只是成功地将一只小龟,由一个缸放进另一个缸」。正如阿芳十年前为了自由离家出走,十年后组建的新家却写满了「不自由」。
早前,阿芳有一件天蓝色的线衣,洗得衣领被撑大,穿上时总是从肩膀滑落。Edward总埋怨让她扔掉,阿芳为了少一事偷偷把衣服藏起来,失去了穿衣自由。

自由,正是《金都》想要探讨的哲学命题。在有限的自由里,每个人都是阿芳,曾经不断的妥协和顺从,直到怎么样也无法和对方取得共识,她可能就会思考,自己有没有离开第二个水缸的选择。
而这个词,却是杨树伟告诉她的。「干嘛结婚?结婚是不自由的」。这个来自福州的男人表面看上去自私势利,为了获得自由身份不惜造假,用油嘴滑舌的腔调不断打趣阿芳急于结婚的事实。却无心栽柳,让阿芳在犹豫不决中,参悟了婚姻的真谛,最后上演了一出「娜拉出走」。

Edward和杨树伟,一个浑浑噩噩的未婚夫,一个看似精明的假老公,导演创作这两个男人并不是要做港男和陆男的对比,虽然某种程度上借杨之口说出「自由」二字实在是对港人的揶揄。
这种手法还体现在别的方面,Edward整日沉迷游戏,生活习惯邋遢,上厕所不关门,在床上剪指甲……以为是个废柴,却发现还是个文艺青年,房间里贴了查理·考夫曼编剧的《暖暖内含光》的海报,就连厕所读物居然也是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导演将夹带私货变成了一种戏谑。
当然,电影有一段严重的割裂,发生在阿芳跟杨树伟回福州的派出所面试单程证时,本来是很好的陆港关系的呈现,但导演因为拍摄许可的问题,福州的取景只能在香港的城中村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的「福州」,土得像国内四五线小县城,阿芳闯入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杨的女友又是一口突兀的四川口音。杨听到女友怀孕后自私地想让其打掉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关键时刻带来「不自由」。以为是渣男的本愿,没想到费尽心思十年拿香港身份证的杨树伟,最后恰恰放弃了。
杨有一个经典的搭讪故事,叫「亚洲蹲」,自称做过研究只有内地人蹲下时是后脚着地的,香港人和美国人都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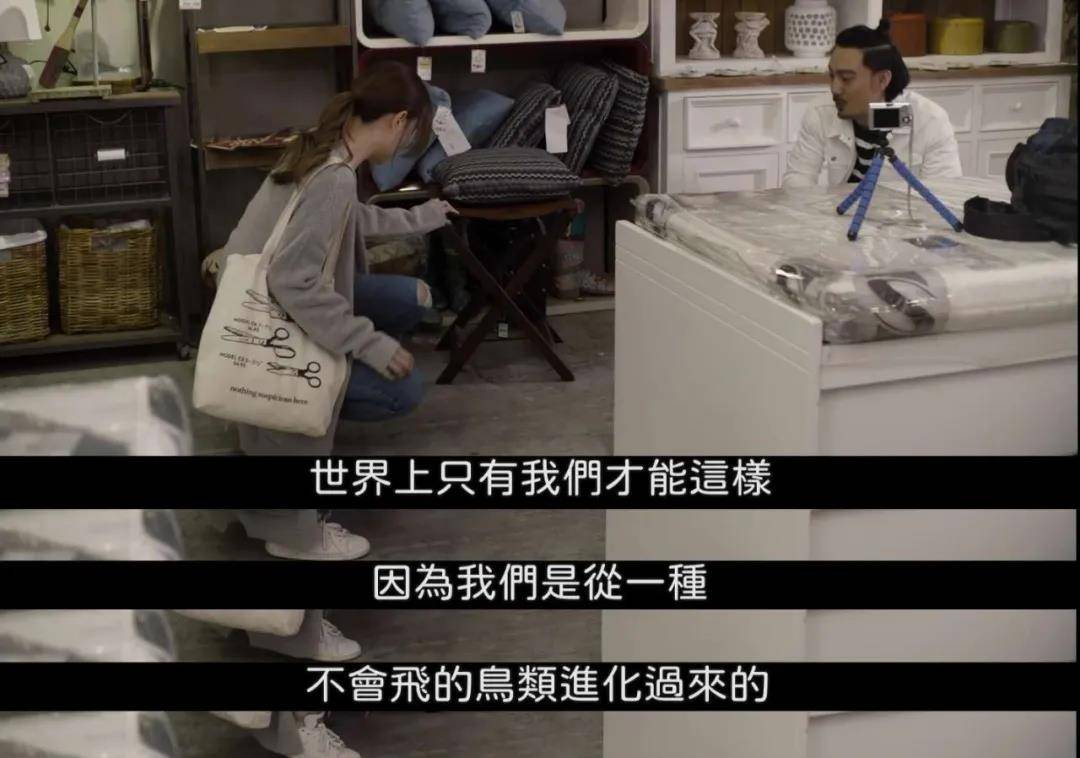
还让阿芳试一试,发现果然不行。
奇怪的优越感是巧妙的反讽,我们明知自己不自由,却嘲笑别人的「自由」,其实无论是故事中的鸟(让人想起无脚鸟),还是被遗弃的乌龟,都暗示了阿芳最终的选择。
所谓荒诞和悖论就在这里,拼命要结婚的人最后选择了出走,穿上天蓝色的线衣,叮嘱Edward收好指甲剪,坐长途大巴,来到福州小农村,和另一个男人完成了一场仪式感的和解。拼命想换取自由的人最后却选择了婚姻,只因为女友肚子里的是男孩?对不起这个貌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确实会掺杂一些重男轻女的不好念头,没去过大陆的导演只凭想象创作确实很刻板印象。

就连很讨嫌的Edward,最后也拼命的想维护关系,买了阿芳的同款乌龟,却再也不能送出去了。
《金都》的结尾,阿芳,或者说是邓丽欣,终于摆脱了世间对自己婚姻的希冀,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穿上喜欢的衣服、关掉手机上男友监控的GPS、下单买了一直心水很久的桌子……她在安静吃面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平静的水缸里,有什么东西鱼跃而出。
当杨树伟最后恭喜她终于要结婚的时候,她淡淡一笑说「李洁冰啊」,意味深长。

是因为求婚前,Edward边剪指甲边跟她讲冷笑话,说自己有一个同学,叫「李洁冰」,还有个妹妹叫「李洁芬」(你结婚)。挣脱婚姻的人恭喜步入婚姻的人,阿芳此刻成为了洪尚秀的《逃走的女人》。
在导演黄绮琳的众多采访中,都介绍了电影的缘起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她也在即将结婚的当口,斩断了一段三年的感情,让My Prince Edward成为前度。同时电影上映前自己的父亲去世,这首部长片处女作,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黄绮琳导演的豆瓣短评
《金都》除了聚焦婚姻这个深刻命题外,也借此对香港现状、陆港关系、乃至去英殖民思想都做出了反思。

电影用「千尺豪宅」来讽刺香港房价高得吓人,买不起房这也是现今香港人结婚的难题。还探讨了同性婚姻,阿芳好奇地问林二汶饰演的阿怡「你説是不是女强人和lesbian才不用結婚?」,却收到了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更难的回答。其实阿芳,包括婚纱店偶遇的老同学Mabel,还有拍婚纱照时和未婚夫闹的不愉快的新娘,可能她们都没想好为什么要结婚,就接受了传统观念中对女人的使命的安排。
电影是恐婚的电影,也是探讨自由边界的电影。

My Prince Edward,暗指的正是英国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王子,太子站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其实细细想来 Edward很能代表现在的香港男人,没有太大野心,只是想玩不想工作,实际上是深受港英殖民的影响,而我们一直称道的「港女」形象,恰恰是和父权抗争,独立自主的。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电影中大陆人作为「第三者」闯入香港人的婚姻,渴望「自由世界」又和自己的行为相矛盾,陆港结婚与否,也影射了陆港关系的「自由」。步入婚姻的一纸契约到底有多少束缚?结婚就不自由,那么不结婚就得到理想的自由了吗?

其中的政治隐喻不言而喻。导演是酷爱调侃的,她自称「我反思婚姻是否是政府的阴谋」。
邓丽欣凭借着出色的表演提名了金像奖最佳女主,没拿影后确实很遗憾,她摆脱了「阿宝」的标签和以往充满稚气的表演,也没有了刻板印象里的港人的浮夸表演,成熟了很多。无论是前半部分的迟钝,还是后半部分的觉醒,邓丽欣都把阿芳演绎的相当妥帖。同样,首次从戏剧表演转战大银幕的朱柏康,也将Edward塑造的可圈可点,包括「老戏骨」鲍起静饰演的婆婆,都让《金都》成为令人惊喜的港片的理由。


有人说它是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大遗珠,有人看了导演的豆瓣后真的要找她「打钱」,导演如果看到,留一个支付宝?
我们在年初也把「迷影精神赏」的最高迷影荣誉授予了《金都》,它确实值得。
在这个金色都市中,人人有怅惘,有怀疑,也有不甘,上世纪的港人意气风发的「can do」,在《金都》里打了一个大写的问号。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娜拉出走又怎样?无人知晓。但正如阿芳学会后脚着地蹲下一样,香港电影的未来可期,对此我仍坚信。
次数不足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


